《我不是潘金莲》译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合适吗?
2024/12/18
我国翻译界对葛浩文把《我不是潘金莲》翻译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发出一片喝彩之声,但不同程度上含有主观的一面。第一种观点认为,葛浩文没有直译为I Am Not Pan Jinlian,是因为西方的英语读者不了解“潘金莲”的文化含义,完全感受不到潘金莲这个文化符号在中国读者心中所产生的反应,因此会造成理解的障碍(伍洋 2017:318;许诗焱、张杰 2020:161)。但是,冯小刚团队的意译和归化的做法(I Am Not Madame Bovary / 《我不是包法利夫人》)不就跨越了这个障碍吗?第二种观点认为,“就故事的荒诞性而言,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表达了一种无中生有的意义,原文中没有出现杀夫情节,用一个不曾有过的情节做题名,其荒诞寓意不言自明”(王冬青 2016:87)。但是,要以荒诞对荒诞,方法何其之多,何必要与原作品产生关联?第三种观点认为,“葛浩文的译文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巧妙地弱化了‘潘金莲’妖艳、淫荡的文化意象,强化了‘李雪莲’含冤申诉的小说主题,与原文的主题契合度颇高”(阮敏 2017:57)。但是,“潘金莲”的人物形象必须要弱化吗?整部小说并没有围绕“谋害亲夫”做文章。这根本不是含冤申诉的主题,又何必拿一个不相关的冤情来强化李雪莲的含冤申诉呢?第四种观点认为,“葛浩文将英译本小说的书名改译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虽然没有突显出轨毒夫的桥段,但情感上是有了‘冤屈’的成分,而且片名制造的悬疑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伍洋 2017:318)。但是,悬疑非要靠一个不相关的情节来制造吗?第五种观点认为,这是创造性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李烨 2019:94)。但是,贴上翻译的标签却讲不出学理上的理由,如果毫不相关的离奇表述就能吸引读者,那么吸引读者的方法何其之多!也有把小说的翻译和电影的翻译放在一起讨论的,例如许诗焱、张杰(2020:161)认为:
电影海报
书封
小说的译者和电影的译者并没有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这个文化符号的“部分意义”只是与小说不相关的部分故事情节。至于翻译的效果,“两个意象相互叠加”还只是“基本再现了‘潘金莲’这个符号在中国读者和观众心中所代表的含义”,至少说明这样的翻译仍然是不够充分的。
有的甚至认为“我没有谋害亲夫”是李雪莲的辩护词,但这类话在她口中确实没有出现过。而且,如果一句辩护词可以成为小说的题目,那么为什么不找一句小说中真实存在的辩护词呢?而如果说葛浩文想通过宣扬或暗示暴力来达到吸引一般市场读者的目的,那么色情(“潘金莲”=淫妇)不是同样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吗?莫言作品中不同地方出现过“破鞋”一语,葛浩文使用过loose woman、whore、harlot等不同的字眼,在这里使用哪个,都可以和“潘金莲”画上等号。
小说原文并没有体现谋害亲夫的情节。为此,小说在叙述时还专门和“潘金莲”作了对比:
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是在与武大郎结婚之后,李雪莲与人发生关系是结婚之前,那时与秦玉河还不认识;更何况,李雪莲并没像潘金莲那样,与奸夫谋害亲夫,而是秦玉河另娶新欢在陷害她。
译者在翻译时是有能动性的。根据葛浩文的小说名翻译实践看,如果他认为原题目不够全面,就会加以丰富,例如他把小说《玉米》翻译为Three Sisters;如果认为原题目内涵不够充分,就会加以改写,例如他把《尘埃落定》改写为Red Poppies(红罂粟),但总体上是指向原文及其意义的,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既然翻译涉及“潘金莲”故事里的一点情节,就难免不让人想到葛浩文的理解可能有误。作者刘震云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我不是潘金莲》书名的翻译: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出国旅游,也变得面目全非。譬如,这个书名英文译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文译为“我不是荡妇”;德文译为“中国式离婚”;瑞典文译为“审判”;还有其他文字,一个语言一个不同的名字,但它们说的是同一个中国妇女。这些书名的相同之处,都避开了“潘金莲”这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性或暴力上,或法律上;不同之处在于,性和暴力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层面和指向,又各有侧重。(舒晋瑜 2016)
译者葛浩文
葛浩文总的翻译原则是“忠实”,所以他更多的时候采取直译的方式。我们随机就能检索到很多直译的例子,如《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推拿》(Massage)、《迷园》(The Lost Garden)、《黑的雪》(Black Snow)、《米》(Rice)、《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红高粱》(Red Sorghum)、《蛙》(Frog)、《浮躁》(Turbulence)、《手机》(Cell Phone)、《生死场》(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呼兰河传》(Tales of Hulan River)、《红夜》(Red Night)、《沉重的翅膀》(Heavy Wings)、《狼图腾》(Wolf Totem)、《贞女》(Virgin Widows)、《第四病室》(Ward Four)等。意译所占的比重不大,如《青衣》(The Moon Opera)、《干校六记》(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尘埃落定》(Red Poppies)、《孽子》(Crystal Boys)等。把《我不是潘金莲》翻译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该是意译,但又不典型,因为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对原文意义的解释。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实非《我不是潘金莲》的内涵,也不是故事的主要内容,所以谈不上是借意译“曲线”达原文之意。
那么,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有没有引起预定英语读者的误解呢?我们来看亚马逊网上英语读者的反应:
我唯一的疑问是,题目和小说内容无关,误导且有危害性。有多少人一看到题目不会认为这是一部犯罪小说呢?(S. Sasic)
看到题目我想李雪莲可能会杀死她丈夫后矢口否认,或者把他杀个半死,使他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A. McCarty)
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原是刘震云用汉语创作的,我想是翻译把它搞坏了吗?(M. Kath)
葛浩文本人没有谈过他为什么要如此翻译,但如果访谈译者本人,他可能会有另外一番说辞,但我们作为研究者作出以上分析也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因为对于译者“缺席”的评价,是建立在评价者握有充分“在场”事实的基础上推理而来的。
本文节选自周领顺教授领衔撰写的《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一书第五章,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购书阅读!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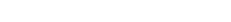
暂无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