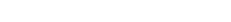性别研究的“大”与“小”(文/段颖杰)
2024/07/05
性别研究的“大”与“小”
(段颖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性别研究已然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显学,就文学研究而言,以性别为议题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不胜枚举,然而质量参差不齐,不少文章存在术语滥用、理论套用、论证浅显、结论单薄等问题。面对这一现状,亟需一本指导性的著作正本清源,以展现文学视角下性别的历史源流、理论沿革和批评实践。刘岩教授在性别研究领域深耕廿载,其主笔的《性别》一书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了性别一词的起源、内涵和指涉,指出“汉语中的‘性别’一词可以指代性别的生理和文化两种属性,但英语中需要区分sex和gender”(P8),而“sex和gender这两个词的分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P11),并在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多重学科维度下讨论了有关性别研究的诸多争论,廓清了性别理论的生发语境。接着是理论本身的细读,聚焦女性主义、男性研究和酷儿理论的发展轨迹、主要观点与核心议题,以“女性主义理论逐渐发展为性别研究”(P34)为主线,详细阐释了“第二性”“女性书写”“男性气质”“性别操演”等关键词。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性别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包括经典研究案例和原创研究案例,为读者提供了立足于文学文本的性别研究范例。最后,刘岩教授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野梳理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的流变和影响,并介绍了性别理论的最新观点和发展趋势。全书脉络清晰、材料丰富、论述合理,作为读者,我从中提炼出两组“大”“小”对比,是为读书心得。
刘岩 等《性别》
学科交叉之“大”与文学研究之“小”
2018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四新”建设中首次明确提出“新文科”的说法,2019年5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正式启动,新文科理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促使不少国内高校积极思考文科专业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与自然科学和新兴科技相结合的可能性。具体到文学专业,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自己框定在一个狭隘的单一学科里,而应该在具体研究中培养跨学科意识。性别研究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来源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对性别的不同认知,同这些学科在近代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与性别相关的政治运动相联系”(P17)。
《性别》一书体现了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作者围绕“度量与描述”向我们展现了生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关性别定义的争论,即性别究竟是可以量化的,还是只能通过文字来描述。注重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现代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些测量性别认同的度量模型,例如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行为量表(behavioral scale)、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的性别角色量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简奈特·斯宾塞(Janet T. Spence)的个人特性问卷(Personal Attributes Questionnaire)和芭芭拉·斯特恩(Barbara B. Stern)的性别身份量表(Sexual Identity Scale)。这些度量模型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划分问题,以看似严谨的科学方法为性别下定义,这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可把定义绝对化,毕竟“实验室数据与人的现实生活行为之间的差异仍是十分微妙的问题”(P20),而且这些量表设定的各项性别特征指标难免有刻板印象之嫌。
相比上述定量研究的“贪大求全”,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就“小”得多了,小至一本书、书中的场景和人物,乃至人物的某句话,都可以引发研究者的思考和分析。性别当然是一种生理特性和社会属性,不过,“有关性别的很多议题和社会规约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传达和延续的,文学作品中对于不同性别人物的塑造及其命运安排,都带有强烈的引导作用”(P25),那么,通过文学作品来讨论性别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所接触到的与性别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其实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阅读体验,正因为我们对于性别已有初步的认知,我们才会在阅读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蝴蝶君》(M. Butterfly)时感到错愕与惋惜,才会对伍尔夫(Virginia Woolf)笔下奥兰多(Orlando)梦幻般的人生经历惊叹不已。而以性别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也时常引导我们将其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为相匹配,进而挖掘出作品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但是,我们需要在跨学科的庞杂和文学研究的具体之间找到平衡点,即其他学科的观点和理论应该成为我们进行论证的支撑点,而不能反客为主,成为论证的对象或目的。那么,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具体该怎么做呢?请看下一组“大”“小”对比。
黄哲伦《蝴蝶君》 伍尔夫《奥兰多》
理论话语之“大”与批评实践之“小”
诚如刘岩教授所说,“在卷帙浩繁的性别理论中梳理出其发展轨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使仅仅考察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性别理论,也需要阅读大量理论和批评文献”(P33)。不过,以时间为轴,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出女性主义、男性研究和酷儿理论的承接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男性开始反思父权制对男性生活的影响,男性研究因此逐渐形成规模”(P70),这表明男性研究是对女性主义的回应和反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酷儿理论则继承了女性主义的批判态度:正如女性主义猛烈抨击父权制,酷儿理论质疑并挑战异性恋常规性(heteronormativity)。
不难看出,性别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是高度政治化的,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然而,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开始借鉴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和观点,女性主义理论变得越来越晦涩。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论断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属还算比较容易理解,但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此基础上的追问就令人费解了:后天形成的又怎样,不还是女人吗?对巴特勒而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实际上只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因为两者的关系是对等的,生理性别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P101)。巴特勒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男女这两种不同的性别,使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那个生产机制是什么。借助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主体概念,巴特勒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指出“性别本身也会自然呈现动态、流动的特征,这构成后现代主体性的显著特征之一”(P47)。
波伏娃《第二性》 巴特勒《性别麻烦》
那么,当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使用复杂的性别理论时,一定要真正弄懂理论的精髓之后再化为己用,把“虚”的尽量说“实”,把“大”的尽量说“小”,把“小”的尽量说得完整和深刻。《性别》一书就提供了值得学习的原创研究范本:“格洛丽亚·内勒小说中黑人男性气质的生成和演变”。该研究以男性气质、经济学和人文地理学为理论依托,从文本入手,具体地探讨了小说人物的男性气质与种植园经济模式和美国南北地理环境的互动和制约关系。更难能可贵的是,研究者在引用理论家观点时作出了合理的批判,如“胡克斯仅仅指出了奴隶制时期种植园的种族权力关系对黑人理想男性气质的洗脑式建构,她并没有关注种植园的黑人男性与该性别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实践”(P164)。反观目前的一些以性别为议题的学术论文,往往落入二元对立或两性平等的窠臼,更谈不上从微观概念和具体语境出发对文学作品做出富有创见的阐发。
即使某项性别研究足够细致入微和发人深省,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还应注意保有开阔的视野和宽容的胸怀。《性别》一书在讲解塞吉维克(Eve K. Sedgwick)对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十四行诗中情欲结构的分析时指出,“她对于男性纽带的关注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究视野”(P147)。当我们选择从性别的角度来阐释某部文学作品时,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这部作品的语言形式和文本内容有着多种多样的阐释可能性,我们不能囿于某一种研究方法中而失去了解其他研究视野的耐心。毕竟,同理心和包容心本来就是性别研究的应有之义:男性和女性都应该跨越自身去体会沉默的另一半世界,这种体察带来的将是人性的拓展和成长。
注: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