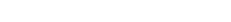重新“认识你自己”——《身体》读后感(文/屈亚媛)
2024/07/05
重新“认识你自己”
——《身体》读后感
作者:屈亚媛,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语言哲学。曾于空军军医大学任教七年。
身体话题由来已久,身体构成了世界图景的基本单元。无论自觉与否,我们每个人与身体朝夕相处、形影不离(P.1)。身体是自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呈现方式。《身体》带领着我从古希腊溯源,从人类早期对身体的构想起航,一路回溯人类社会不同时期对身体内涵和外延的认知差异,最终落脚到身体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文学的维度理解身体本身如何被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的力量所标记与改变。
《身体》一书让我重新认识到柏拉图、笛卡尔、尼采、梅洛-庞蒂、福柯对身体问题的关切。自古希腊到19世纪中期,身心观都呈现出分裂的二元对立的状态。柏拉图,这一让西方两千年哲学都为其思想做注脚的哲学家认为,灵魂是“万物的尺度”,身体被忽视和贬损,身体是被束缚在洞穴内的物质,基于此得到的知识也只能是偏见,只有抛弃身体,才能重见真理的光明。至基督教产生,对身体的禁欲态度非常明确,无论是圣•保罗对“灵与肉的区分”抑或圣•奥勒留•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看法,都是对柏拉图身体思想的隐秘转换。古希腊锻炼身体的习惯被抛弃,身体隐蔽在复杂和华丽的装饰之下,身体的沉默史,以及先行的自我惩罚以替代疾病对身体的惩罚的观念,全都为了尽可能地灭绝人欲,从而更接近上帝。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身体沦为了工具和机器,且是邪恶的东西。
柏拉图“洞穴之喻”,图片源自网络
那么被称之为“现代哲学之父”、现代理性哲学奠基人的笛卡尔又是如何看待身体问题呢?《身体》认为,笛卡尔深受柏拉图影响,认为“纯正和精炼的思想是真正知识的起源”,主张在“求知”的过程中,不受身体之惑。世界既然由“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组成,那么只有代表“理性、稳定性和真理秘密”的心灵可解开知识和真理的秘密,身体作为一架机器,根据因果原则和自然法则起作用,实在太不可靠了,常常是“错觉和幻想”的代表。笛卡尔的二元划分标志身体被纳入客体范畴,将精神从身体中分离出来。这种分裂的好处在于从此理性主义带来启蒙运动,生物医学得到发展,心灵成为人文学科的主题;弊端是身心本是相依的统一体,绝对分割让身体及其功能有了羞耻感。但是,走向极端的身心观已经为19世纪中期的身体回归埋下了伏笔。
笛卡尔,图片源自网络
尼采称,“一切从身体开始”,梅洛-庞蒂认为,“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身体哲学”转向不仅是对西方传统的思辨哲学的纠正,也标志着当代哲学的“反形而上主义”。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置于哲学显著位置的哲学家,世界不再与身体无关,而是身体和权力意志的产品。意识、精神、灵魂成为身体的产物(P.43)。尼采发出“上帝已死”的呼声,建构了谱系学的身体哲学,将身体作为一切价值的开端和归宿。这位极具革命性的思想家将哲学的目光由形而上转移到了真实的生命。20世纪80年代,我国青年知识男女对尼采的热爱很是炽烈。据说不会几句尼采名言,就无法谈笑风生。尼采是个“疯子”,因为他要清算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弊病,如传统道德、基督教文化以及理性主义(科学)给西方文明带来的不可名状的危机。他认为表面的繁荣盖不住工业大发展带来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弊病。热爱生命的尼采认为这些都是削弱生命活力的逆生命之流。
尼采,图片源自网络
重大的哲学思想有时并不是为了破除旧有而产生,有时是在新旧交替之时浮出水面。哲学家的思考也并非凭空出现,他们往往受之前的哲学观影响而不自知。虽未言明身体,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却将反理性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也将“身体”置于推动社会历史文明发展的新高度。除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贡献,20世纪后期将身体研究推向显学地位的学派中,贡献最大的当属起源于法国、以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身体现象学派。梅洛的哲学被称为“含混的哲学”,他认为,身体具有经过长期自然进化形成的“生存智慧”,是具有“身体图式”和“行为结构” 、能行动的、具有“默会知识”习惯的自动化身体。身体现象学将身体提升到主体的地位,身体不再是对象性的客体,而是革命性地实现了对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体之分的超越(P.65)。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消解了意识哲学,意识主体的死,意味着“身体主体”的生,身体完成了其逐渐回归的路程,并将进入身体理论的狂欢阶段(P.68)。
作为尼采的信徒,福柯为20世纪身体理论发展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他讨论了规训中的身体、权力关系中的身体和两性关系中的身体,为20世纪后期文化研究的身体转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启示。福柯认为,权力同大众传媒、社会文化、道德法制互相结合,对身体的控制和支配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身体也成为权力和大众文化操控的对象,成为消费文化塑造的对象。到此,《身体》一书详尽、清楚地梳理出身体问题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的起源、起伏和现状。那么,身体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又是怎样呢?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虽成就斐然,但并没将身体完全从精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随着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诞生,身体反而再次被完全遮蔽,文学作品中,身体话语和意象难觅踪影。但在理性占据压倒性地位的18世纪有一个例外,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身体意象就有身体造反的意味。通过“巨人国”和“小人国”的身体现象,作者似乎是在表达:人的眼界视野与道德高度和他的身体具象不无关系(P.157)。在勒皮他岛游记中,斯威夫特讽刺了忽视身体需求、压抑身体及其本能的可笑与荒唐。斯威夫特作品中数量繁多的身体意象,构成了斯威夫特针对理性至上传统的“身体造反”。
《格列佛游记》,图片来自网络
苏联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巴赫金是第一位直接将身体研究回归到文学内部且自成一家的思想家。他在《巨人传》的艺术评述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的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现象等。巴赫金反对蔑视身体的思想,为身体正式进入文学研究的殿堂开辟了一条借鉴之路。法国作家杜拉斯主张原初体验指向现实关怀,张扬身体的欲望叙事和审美快感。如果一个活的、具备经验的身体不在,如何真实地进行写作?即便是身体疾病也会严重影响一个作家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如结核病之于卡夫卡的阴郁、肺炎之于普鲁斯特的耐心、哮喘之于鲁迅的激愤等(P.102)。比起用精神意识看问题,还是身体最诚实。
受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思潮影响,身体研究也针对女性身体展开。流行文化对女性的身体塑形展开冲击,可以说,歇斯底里症、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等疾病不仅是医学现象,还是文化的复杂体现。女性身体处于社会控制的一个特殊场域。理性被视为殖民性的、规训的和男性的;身体是他者,与欲望、非理性相关,可被殖民,且是女性的(P.121)。女性身体被视为未被规训的,而对缺乏规训的恐惧演变为对女性身体的控制,这是一种新型的身体压迫。
《身体》探寻了19世纪神经性厌食症的出现与维多利亚时代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对当代的女性身体问题同样有启发意义。“某一文化中产生的精神病理学,远非反常或失常现象,而是那种文化中诸多问题的集中体现”(P.135),比如以瘦为美和进食障碍。如果回到福柯关于权力的分析,可以看出,权力的有效运作迫使女性寻求控制身体的方式,如化妆或抽脂。控制身体是生存策略,也是价值肯定,好像只有如此才能成功。整个社会默许了这种权力运作,而且得到女性自身的默许。也许不存在让女性变瘦的阴谋,只不过因为权力过于分散,也过于隐蔽,但的确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为特定文化中的男人和女人看待自己身体时所感到的压力负责任。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图片来自网络
《身体》发现当下社会的这些现象和维多利亚时期对待身体的问题类似。维多利亚文化也许催生了当代美的标准。当代女性将身体视作可以控制和规训的对象,受制于意志力与凝视。当代女性处于一个大众媒介和社会氛围所构筑的边沁式的圆形监狱中,为拥有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身体而节食、戒食,导致各种进食障碍。这种局面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味,女性需切实应对社会文化中对苗条身材的痴迷问题。因为除了身材之外,女性应该拥有更多能够为她们带来权力与成就的渠道。总之,从文学作品中时常被忽略的现象入手,挖掘出背后隐藏的文化现象与政治意图,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值得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
此外,疾病是人类身体健康的另一面,疾病不断提醒着我们身体的存在(P.164)。《身体》还介绍了美国知识分子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揭示的疾病文化隐喻的现象。《疾病的隐喻》也是探讨身体疾病和文化认知之间的社会批判的一部力作。
《疾病的隐喻》,图片来自网络
疾病,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进而又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P.108)。底层逻辑是结核病、艾滋和癌症等病症难以治愈,给人们造成神秘和恐惧的印象,但它们又一次次因为不同的目的而被重新阐释。如今,隐喻式阐释疾病使之成为社会共同想象的意象过程仍在继续。无论东西方,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联想所塑造的隐喻都在遮蔽疾病原本的真相。而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或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隐喻式的思考(P.165)。
无论身体理论在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中如何发声,围绕身体的研究最终会回归于对社会文化、权力话语或政治经济现实的解读。铭刻了社会文化书写意义的身体是一个中介,是用来观察世间万象的“万花筒”。打破了原有研究范式后的身体研究,可继续聚焦于社会中的身体、政治中的身体、文化中的身体等方面。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下,无论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还是量化研究手段,抑或是混合研究方法,关于身体研究问题的底层逻辑还需要追溯至与身体哲学相关的哲学思潮。或可以理解为,方法论取决于具体研究问题之所需,而认识论还需辨别哲学脉络。感谢《身体》,让这个世界更加明晰,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