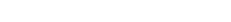一位编辑的《我的阿勒泰》观剧感想
2024/07/04
(图片源自网络,下同)
剧版《我的阿勒泰》描绘了主人公李文秀在城市碰壁后,来到阿勒泰这片辽阔天地下,同妈妈张凤侠、奶奶一起融入哈萨克牧民的生活,与巴太、托肯、库兰建立真挚的情谊,在这片陌生又新鲜的土地全身感受、体验的故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人与自然的共生、代际的冲突与调和,人与人的矛盾与信任,都在阿勒泰的日出日落间缓缓展开,犹如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沉醉在这片土地的无尽魅力中。这部剧涉及的主题很多,网上也不乏讨论,这里主要结合曾经编辑的学术图书作一点个人的分享。
我的家园,传统与现代
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哈萨克族的家园展开,这里有宽旷的大地、成群的牛羊、闪光的溪流,恣意生长的森林、起伏的草地、斑斓的野花,族人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劳作、生活,在对传统的延续中慢慢接受和应对时代的改变。他们置身其中,像是当地万物的一环,没有对立,没有割裂,自自然然。即便哪天他们必须离开这里,他们心中对于辽阔土地的眷恋和对这片土地上自然、人际秩序的传承亦不会改变。
《民族》书里写道,“乡土的主题和空间、扎根等概念密不可分,连接着我们关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记忆。高山、荒漠、森林、草原这些纯粹的自然存在经由作家的书写成了寓意深远的意象。在他们的论述中,空间不再是没有温度、客观中立的纯粹存在,而是有着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的精神寄托。”
《生态女性主义》里说,“每个人都安泊于家园中,这片我们本能熟知的土地。只有了解地域的依存性,我们才能像树木般地生根。倘若我们忘却了与地方的联结,或者忽视和否认与泛性土地的关系,我们将成为萎顿的物种,失去生存的热望和希望。”
在巴太父亲苏力坦的质问中,“我喜欢的生活一样样地消失。鹰不能养了,猎不能打了……大家转场,也不再走仙女湾小道……这个世界一定要这样发展吗?”我们感受到了新旧交替的碰撞,看到了这片土地的一些变化,虽然他作了妥协,但内心深处还有很多应是根深蒂固的。文秀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但在家园的变革存续中,在时代的洪流中,又有什么是可以抓住的呢?我想是土地给予我们的希望,是万物共生的一体感,是内在的约束与自足,是对自我生命的追寻。
《民族》 《生态女性主义》
我喜欢你,我清楚地看见你
作为女性导演创作的作品,剧中的女性角色无一不让人欣喜,通透豁达又不乏温柔细腻的张凤侠,单纯敏感又坚定的文秀,直率可爱的托肯,质朴善良的库兰,等等。她们的智慧、热爱、喜悦、忧伤都像你我一样真实。在她们的世界中,情感是那么重要又自在的存在,她们可以极力地奔赴热爱,即使受伤,也可以再回到自我,自愈,自洽,继续坦然的生活。
在面对观众质疑剧中人物恋爱脑的时候,导演回应道,“大家会否定恋爱脑,但我认为是另外一种方向的慕强。你认为理智,冷酷,自私,只爱自己,才是一种强大的话,那是偏颇的。我觉得女性身上的多情、浪漫,甚至是情绪化,很容易跟别人共情,她的包容,她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心,它也是一种强大。”我想这应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女性不是社会规训的产物,不是与男性的对立,她们同男性一样,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调适着自己的角色,与周边的一切建立联系,发挥着自己的价值。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性别问题有不同的规约和矛盾,也有其适当的革新和适应方式,而作为个体,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特性、渴求、期待、价值,感知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生命方向,也尊重不同的群体。如《性别》前言所说,“性别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生存,同时也涉及群体间的理性交往。毕竟对于性别的追问,就是走在苏格拉底所言‘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
女性书写或者女性呈现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身体,女性身体以其全部存在,包括感官、皮肤、神经、运动习惯及其内含的历史和心理积淀,去深入感知世界的存在,去发现,并内化为个人的真实体验和思考。剧中说,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意思就是,我清楚地看见你。当我们想到文秀初见巴太时,她就那样专注地看着那个骑着骏马的高大男孩,从远到近,再从近至远;而他们再次在林中碰面时,也是毫无言语,只是看见。在情感的蔓延生长、离散聚合中,他们眼神的碰撞、闪躲、逃避、欲说还休似乎已在不经意间诉说了所有的情愫和故事。
《性别》 《身体》
《身体》里写道,“当一种交织在看与可见之间、在触摸和被触摸之间、在一只眼晴和另一只眼晴之间、在手与手之间形成时,当感觉者—可感者的火花擦亮时,当这一不会停止燃烧的火着起来,直至身体的这种偶然瓦解了任何偶然都不足以瓦解的东西时,人的身体就出现在那里了。”
当张凤侠安静地在阳光下擦着她的长发,展示她女性气质的一面时,我们明白她已准备好迎接自己新的爱情。当剧中的女性在公共浴室中缓慢地搓洗着自己或亲人的身体,或哄抱安慰着赤裸身体哭泣的孩子,或和陌生的她者在这里和声歌唱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没有亵渎的纯粹的美,这样彻底放松的自然裸露被赋予了某种精神性的意味,蕴含着回归和温暖的感动。“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身体成为意义的根源和出发点,开始了爱与悲伤、感激与怀念、美与眷恋的书写。
我的田园牧歌,碰撞与成长
在整个故事中,田园与城市一直与文秀和巴太的成长紧密相连。剧中纯天然的令人治愈的风景催生出我们对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渴望,甚至产生一种逃离的感觉,但也真实地呈现了当地劳作的不易、女性家庭地位的不平等、生存环境的艰苦,等等,避免了传统田园牧歌书写中单纯的怀旧、隐退和赞颂主题,从而达到一种闲适与艰苦的微妙平衡。如《田园诗》中写道,“隐退与回归彰显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张力……田园借隐退来远离现实的焦虑和矛盾,但最终却通过回顾向现实传递智慧。”《我的阿勒泰》又何尝不是如此,让人对其中的种种缩影作深入的思考。时代的影响与作者及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感受、发展交织相连。
空间的转移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跨地域的空间体验和文化碰撞会加速青年对环境和自我的认知,在城市和田园的迥异对比中,这种探寻可能会更加深刻。文秀也曾有很多自己固有的见解,但在一次次与牧民的交往中被不断地冲击、打破、重构,她看到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的制约是有限的,也是足够的,“看到人类活动与自然万物活动的相同节奏,感受到乡村社会曾有的‘古老的自由’与自然界生灵所享有的‘大自然无序’之间的深层联系”(《田园诗》)。在经历友情、爱情的美好和伤痛中,她不断地寻找自我的心灵家园和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位置。
《成长小说》里谈道,“何谓自我?一个人只要还按照某种普遍性的东西来确定自我,那么这个自我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成长会考察社会要求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关系……这个个体尚年轻,像一张白纸一样对外部世界开放,他/她用其心智和情感吸纳各种不用的经验,其卓越在于其孜孜不倦对自我的追求。”
而巴太的成长,也在家庭的变化、情感的变化中悄然发生,在不断的冲突和破碎中重新建构,在不停的叩问内心中获得对社会规则和自我价值的认同。他最后的回归,或许也暗含了多年漂泊后对传统的延续和责任。但无论在哪里,成长一直在发生,它永远是进行时。
《田园诗》 《成长小说》
关于这部剧,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回味,比如母女俩关于何谓有用的对话,族人送别木拉提的仪式,巴太与踏雪相处的每一幕……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学术视角的看待方式,比如跨媒介改编的叙事风格与意义,作者的生态研究、空间对人物心理与形象的塑造,动物伦理,等等,我想,这并不是寻求一种刻意的解读,而是借助这些多元的视角,让我们加深对作品的认知,也在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中滋润个体的生命。